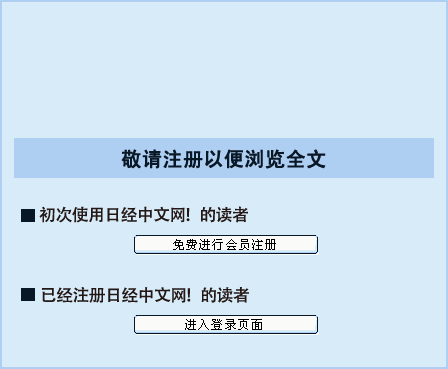东京眼(303)一人一个沙士回忆 (上)
2020/02/06
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健吾:我是一个没有青春的人。
小时候,我的父母都一直跟我说,家贫,一定要念好书。我有一个舅父,他念书好厉害,他是早年的香港大学毕业生,毕业后结婚生子,四仔主义的支持者,女儿,即是我的表姐都是念名校的。都是优秀的人,在社会的定义中,绝对地,不可置疑地优秀的人。
我妈看着他,也许就是最成功人士的代表了。所以,她一直着我念我,当男生一定要英文数学都要好,英文数学都好,你才会是一个有用的。他们相信的教育,是一种英才教育的迷思,就像日本战后的教育妈妈,教育人生花道之类的想像:只要你好好的念,念到一个位置,入了好的小学,就可以进好的中学。在好的中学,就可以考好试,考进好的大学,那你即使是一个工作能力普通的人,你都可以过中产的生活。那就是所谓人生的花道:春天赏花秋天看红叶冬天去洗一下温泉,过年的时候挤一下新干线回乡见一下老父老母,再花尽一生的力气做一份你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想做的工作,跟一些你根本不在乎或是不喜欢的人喝酒打闹,养活自己的那个叫「家」的包袱,直至退休,然后又不知道自己时间如何过,还可以做什么,然后一直等着,就是死。
我是一直以为,读完大学,一切就会很美好。所以我一直都没有青春:我没有心如鹿撞的恋爱,也没有同生共死的「运动场上」战友。我的少年时代,一直都讲义和考题之中。
直至沙士(SARS,非典)之后,我的青春,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才出现。
那是「实现梦想」的一段时间,很青春。
2002年,我刚刚毕业,那时候,我以为我自己会直接到日本赴学。那时候,是因为毕业的某种迷失的状态:我终于完成了父母的期许了,他们看到我大学毕业很高兴,就好像是他们人生最厉害的成就。但是,我还是在想,我念的科系不是「专业」的科系,跟我同宿舍的朋友不同。他们在香港,选择了很清晰的路,他们有一个专业的资历,会计师、律师、医生、牙医,他们可以进入一条明显的路,选择只有一个:做或不做,没有「做什么」的难关。而我念的是新闻系,新闻毕业生的薪水,在香港是出名低的。我的同辈,即今年30后半左右的,若然仍在当记者,月薪有两万五千到三万港元(约42万日元),已是不错的收入。但他们也几近肯定难以在香港置屋租房的。在香港,市区的小单位,一房,约300呎左右的,都要15000~18000港元(24万日元左右),会占他们的月入一半以上。
这样子的生活水平,钱帐面是赚多了,却不可以生活下去。于是我一直在逃避,希望自己可以有多一点选择,也等自己一直完成某一种梦想:「会说日语」这个梦想,就考了奖学金(我之前说过我家贫的),准备留学。但不知道为什么,大学的申请部门那个行政官员,可以「忘了」把我的申请书投到日本当局,即使他们决定收录我(指导老师,大学部门都答应了),就是因为大学当局的那女人,忘了把我的申请书投到日本,我的奖学金没了,我的留学大计也没了。而在那一年,我被迫留在香港。他们的处理方法也非常简单,没有要求我要签什么保密协议,只是说下年会为我们申请,一定会申请到为止。就这样而已。
我带着一个不知道会不会实现的「承诺」(亲爱的你应该知道我在去日本留学之前,都以为日本人会很注重承诺的民族。但后来我完成学位之后,念的书告诉我,你得要明白民族论述的盲点,就是很容易忘却人的多样性。正如我们以为日本人都会很听话,君不见有两位于2020年从武汉回到东京的日本人拒绝入院接受检查或隔离吗?这样子的论述是有局限性的),在香港待了一年,那时候,我们经历了沙士。
全香港,七百万人,不知道为什么,天天担惊受怕,生怕自己会有一天走不过去。
那时候,我们记得什么?有一种悲伤是,我们天天上班,之后赶着回家。天天看新闻,都追读报道:看着那个天天加长的更新地址列表,自己住的大厦,会不会成为「中奖」名单?每天回家,都只可以追看新闻台的反覆重播,在网路用的沟通软件叫ICQ,要写博客顶多是xanga 或是个人新闻台,然后我们听到一个叫张国荣的歌手跳楼身亡。整个都市,除了忧伤,还是忧伤。原来,面对这个病毒风暴,香港人也好,全世界的人也好,都只有等。戴上口罩,只看到眼睛,人与人的距离很远……想不到的,或是想像不到的,是我的人生,要再一次经历沙士。
只是更大规模而已。
我的第一个变改是:我更立下决心,一定要做一件「青春」的事。我去了日本念书,不再理会,沙士后的香港……
沙士后,有什么改变吗?香港人,有因为我们在生与死之间的距离那么近而有什么变改吗?
 |
健吾 简历
80年生,香港专栏作家、香港商业电台节目《光明顶》、《903国民教育》主持,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研究学系及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讲师。著书超过二十七本,主力研究日本东亚流行文化软实力及多元性别关系等议题。
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,不代表日本经济新闻(中文版:日经中文网)观点。
版权声明:日本经济新闻社版权所有,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或部分复制,违者必究。
金融市场
| 日经225指数 | 28493.47 | 336.50 | 04/14 | close |
| 日经亚洲300i | 28493.47 | 336.50 | 04/14 | close |
| 美元/日元 | 132.42 | -0.60 | 04/14 | 15:15 |
| 美元/人民元 | 6.8381 | -0.0298 | 04/14 | 07:14 |
| 道琼斯指数 | 34029.69 | 383.19 | 04/13 | close |
| 富时100 | 7843.380 | 18.540 | 04/13 | close |
| 上海综合 | 3336.1530 | 17.7892 | 04/14 | 14:05 |
| 恒生指数 | 20405.12 | 60.64 | 04/14 | 14:04 |
| 纽约黄金 | 2041.3 | 30.4 | 04/13 | close |
・日本经济新闻社选取亚洲有力企业为对象,编制并发布了日经Asia300指数和日经Asia300i指数(Nikkei Asia300 Investable Index)。在2023年12月29日之后将停止编制并发布日经Asia300指数。日经中文网至今刊登日经Asia300指数,自2023年12月12日起改为刊登日经Asia300i指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