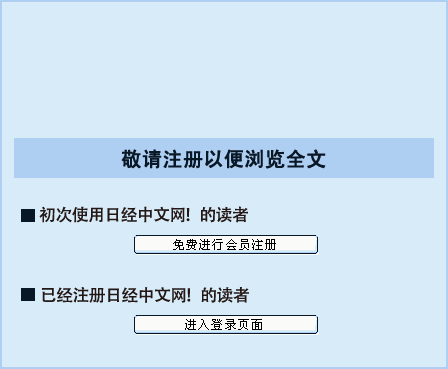东京眼(16) 日常机械白日梦和小事化大的关係
2014/05/29
日经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健吾:于台湾工作的日本友人高桥先生常说,他学了中文这些年,很爱看台湾电视。尤其是,台湾人总爱把无聊的小事,放到电视新闻中,每小时重覆一次。屁大的小事,都好像说得很重要似的。
比方说,最近,台湾,有拉麵店放了一台自动贩卖机,各大电视台就做了一条专题报道,指这种「日式自动贩卖机」终于来台了。「有什么特别,这些东西在日本每家食店几乎都有。但台湾的电视台就是可以说很多东西:顾客的反应,店员的反应,还找来学者专家来分析这种『自贩机』会不会影响就业生态云云。」高桥先生在Line传我简讯的说。
我们活在一个现代社会,一个我们视为先进及文明的社会,人人手边都有很多机器。当手边的机器「方便」了,事情就很容易小事化大。以前,在台湾看到电视做什么,顶多是少部份的专栏作家、记者或是有机会在电台发声的人,才会有机会跟人家说台湾的电视做什么。现在,任何人都可以告告诉任何人了。我们都习惯身边有简讯狂、 自拍狂、Twitter 狂:没有手机、没有简讯、没有Instagram,他们的生活都没有意义。不,也许是反过来的:没有手机,没有简讯,没有Instagram,他们或许会过一些很沉闷的生活。为了上载「精彩」的人生,香港人会花很多时间去做很多他们不会做的事。如在一个星期天去咖啡店,叫一杯 English Tea Latte (即是热奶茶,加香草糖水),在咖啡桌上放一本书,拍一张照片,放上网,然后告诉全世界,「他很有生活」。
每每看到人和机器互动,我也会想,究竟我们真的是方便了,得到多了;或是麻烦了,失去多了。在网上,流传一句香港的流行爱情小说教母亦舒小姐有一句名言:有一件新东西,我们就要服待他。机器是服务我们,还是我们在服务机器?比方说,自贩机的出现,就令心理学家想出一个状态:究竟我们真的接受自动贩卖机这种「文化」对我们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吗?简单一点而言,在资本主义社会,我们都习惯有问题发生的时候,用钱解决。口渴了,我们去买饮料水。肚饿了,我们去便行商店买饭团。自贩机的出现,就更加深我们现代人有事情发生的时候,就立即用钱解决(plug-and-play quickfit)的心理状态。
而手机的出现,就更令我们把很多不值一哂的资讯放大广传。比方说,以前在香港的双层巴士上,如果有一个精神有点失常的乘客在不断的高唱郑秀文的《终身美丽》你会怎么做?以前,大抵是戴上耳筒,听着Walkman随身听,等自己到站或是那位「歌者」到站。现在?即时、立刻、应该有几十人拍摄短片,然后流传到各社交网站了。
在日本读书的时候,都有听过日本朋友说,日本人比较着重「公众地方」的礼貌。在交通工具上他们不会像我们香港人一样,放大嗓门高声聊天。
那些在欧美地区流行的「新世代电子用品使用礼仪」之类的小书,记载用手机的时候要紧记:
确保使用手机不冒犯他人是你的责任。
通话时要与人保持距离。
在密闭的公共空间,如电影院,最好不要讲电话。
注意声浪。讲手机时要轻声,也绝不可以用免提喇叭公开肆谈无忌。
有什么私人、重要的东西,请见面的时候说。
同桌吃饭别边吃边讲。长话短说。可以用简讯说就用简讯,发简讯时也不时和别人保持眼神接触。
还有,最重要的,是:美术馆、图书馆、演奏厅、电影院、医院、葬礼、会议、课堂,都不应使用手机……
以上种种戒律,在日本都好像是「应然」之事。还有更多更严格的规矩没有被列举出来:在火车内不得聊电话,要谈就要到讲电话的空间。在关爱席附近的位置不得使用手机,因为有些装有心脏起搏器的人也许会受电波影响。看影片的时候要使用耳筒,不要全车人也听到你打机的声音……
虽然,我也听过很多日本的大学教授投诉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手机。但当教授们提醒他们在课堂用手机的时候,还好同学还会有一丝悔疚。在日本这种怕骚扰人的文化氛围下,在日本,大中华地区很流行的微信就一定不能登大雅之堂。在香港,当你在街上看到很多中国大妈放大嗓门在讲电话的同时,你也不难发现那些身穿Chanel Hermes 的中国富二代拿着手机录短讯,然后在火车肆无忌惮的听短讯。有好几次,我问用口讯功能的艺人朋友,为什么他们要录口讯,而不打字。他们都跟我说:「是这样的呀!微信是这样玩的。打字很麻烦嘛……」
每次收到这种口讯,我都得要插好耳筒才敢听……
以上一千三百多字,对很多香港人来说,也许只是小事。为什么要有礼貌?为什么要像日本人?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,既然大国崛起了,大家都看着中国办,我们怎么要学别人呢?哈哈哈哈哈。
健吾 简历
80年生,香港专栏作家、香港商业电台节目《光明顶》、《903国民教育》主持,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研究学系及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讲师。著书超过二十七本,主力研究日本东亚流行文化软实力及多元性别关係等议题。
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,不代表日本经济新闻(中文版:日经中文网)观点。
版权声明:日本经济新闻社版权所有,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或部分复制,违者必究。
比方说,最近,台湾,有拉麵店放了一台自动贩卖机,各大电视台就做了一条专题报道,指这种「日式自动贩卖机」终于来台了。「有什么特别,这些东西在日本每家食店几乎都有。但台湾的电视台就是可以说很多东西:顾客的反应,店员的反应,还找来学者专家来分析这种『自贩机』会不会影响就业生态云云。」高桥先生在Line传我简讯的说。
我们活在一个现代社会,一个我们视为先进及文明的社会,人人手边都有很多机器。当手边的机器「方便」了,事情就很容易小事化大。以前,在台湾看到电视做什么,顶多是少部份的专栏作家、记者或是有机会在电台发声的人,才会有机会跟人家说台湾的电视做什么。现在,任何人都可以告告诉任何人了。我们都习惯身边有简讯狂、 自拍狂、Twitter 狂:没有手机、没有简讯、没有Instagram,他们的生活都没有意义。不,也许是反过来的:没有手机,没有简讯,没有Instagram,他们或许会过一些很沉闷的生活。为了上载「精彩」的人生,香港人会花很多时间去做很多他们不会做的事。如在一个星期天去咖啡店,叫一杯 English Tea Latte (即是热奶茶,加香草糖水),在咖啡桌上放一本书,拍一张照片,放上网,然后告诉全世界,「他很有生活」。
每每看到人和机器互动,我也会想,究竟我们真的是方便了,得到多了;或是麻烦了,失去多了。在网上,流传一句香港的流行爱情小说教母亦舒小姐有一句名言:有一件新东西,我们就要服待他。机器是服务我们,还是我们在服务机器?比方说,自贩机的出现,就令心理学家想出一个状态:究竟我们真的接受自动贩卖机这种「文化」对我们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吗?简单一点而言,在资本主义社会,我们都习惯有问题发生的时候,用钱解决。口渴了,我们去买饮料水。肚饿了,我们去便行商店买饭团。自贩机的出现,就更加深我们现代人有事情发生的时候,就立即用钱解决(plug-and-play quickfit)的心理状态。
而手机的出现,就更令我们把很多不值一哂的资讯放大广传。比方说,以前在香港的双层巴士上,如果有一个精神有点失常的乘客在不断的高唱郑秀文的《终身美丽》你会怎么做?以前,大抵是戴上耳筒,听着Walkman随身听,等自己到站或是那位「歌者」到站。现在?即时、立刻、应该有几十人拍摄短片,然后流传到各社交网站了。
在日本读书的时候,都有听过日本朋友说,日本人比较着重「公众地方」的礼貌。在交通工具上他们不会像我们香港人一样,放大嗓门高声聊天。
那些在欧美地区流行的「新世代电子用品使用礼仪」之类的小书,记载用手机的时候要紧记:
确保使用手机不冒犯他人是你的责任。
通话时要与人保持距离。
在密闭的公共空间,如电影院,最好不要讲电话。
注意声浪。讲手机时要轻声,也绝不可以用免提喇叭公开肆谈无忌。
有什么私人、重要的东西,请见面的时候说。
同桌吃饭别边吃边讲。长话短说。可以用简讯说就用简讯,发简讯时也不时和别人保持眼神接触。
还有,最重要的,是:美术馆、图书馆、演奏厅、电影院、医院、葬礼、会议、课堂,都不应使用手机……
以上种种戒律,在日本都好像是「应然」之事。还有更多更严格的规矩没有被列举出来:在火车内不得聊电话,要谈就要到讲电话的空间。在关爱席附近的位置不得使用手机,因为有些装有心脏起搏器的人也许会受电波影响。看影片的时候要使用耳筒,不要全车人也听到你打机的声音……
虽然,我也听过很多日本的大学教授投诉学生在课堂上使用手机。但当教授们提醒他们在课堂用手机的时候,还好同学还会有一丝悔疚。在日本这种怕骚扰人的文化氛围下,在日本,大中华地区很流行的微信就一定不能登大雅之堂。在香港,当你在街上看到很多中国大妈放大嗓门在讲电话的同时,你也不难发现那些身穿Chanel Hermes 的中国富二代拿着手机录短讯,然后在火车肆无忌惮的听短讯。有好几次,我问用口讯功能的艺人朋友,为什么他们要录口讯,而不打字。他们都跟我说:「是这样的呀!微信是这样玩的。打字很麻烦嘛……」
每次收到这种口讯,我都得要插好耳筒才敢听……
 |
以上一千三百多字,对很多香港人来说,也许只是小事。为什么要有礼貌?为什么要像日本人?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,既然大国崛起了,大家都看着中国办,我们怎么要学别人呢?哈哈哈哈哈。
健吾 简历
80年生,香港专栏作家、香港商业电台节目《光明顶》、《903国民教育》主持,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研究学系及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讲师。著书超过二十七本,主力研究日本东亚流行文化软实力及多元性别关係等议题。
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,不代表日本经济新闻(中文版:日经中文网)观点。
版权声明:日本经济新闻社版权所有,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或部分复制,违者必究。